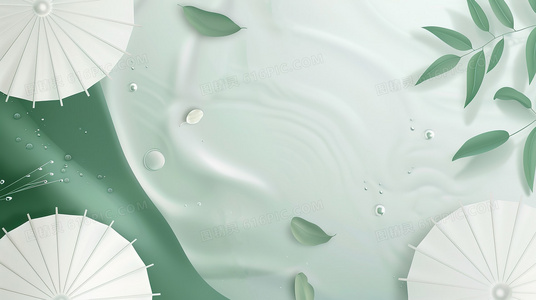黄河水浑黄如土,日夜奔流。人们称它为母亲河,但在我眼中,它更像一位沉默的见证者,将无数未说完的故事裹挟在泥沙中,送到我的面前。

我叫李振河,今年五十七岁,在黄河中游这段水域捞尸,已经整整二十三年。
第一具:红棉袄的小女孩
我捞起的第一具遗体是个小女孩,约莫七八岁,穿着褪色的红棉袄,头发上还系着半截红头绳。
那是1998年的冬天,黄河刚解冻不久。女孩的父母从甘肃一路寻来,见到遗体时,母亲瘫倒在地,父亲则死死盯着女儿肿胀的小脸,一言不发。
后来我才知道,女孩是去河边给生病的奶奶打水时滑落的。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塑料水壶,里面灌满了黄河的泥沙。
“她奶奶三天前走了,”女孩的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要喝孙女打的水。”
那件红棉袄,我至今记得颜色。
无名者的尊严
不是每具遗体都有人认领。黄河太长,太宽,有时一个人消失了,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河流。
我曾捞起一具年轻男性的遗体,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有右手腕上纹着一行小字:“此生不负”。他的指甲缝里嵌着细小的金屑——后来警方确认,他是上游金矿的工人,矿难后家人不知去向。
按照规定,无人认领的遗体会被火化,骨灰撒入黄河。但我总会在记录本上为他们编号,并尽可能记下特征:左肩有胎记的中年女性;戴着断了链的怀表的老人;脚踝系着红绳的少女...
他们曾是某人的孩子、父母、爱人。即使故事无人倾听,至少应该被记住曾存在过。
最漫长的一夜
2005年夏天,一艘渡轮倾覆,四十二人遇难。我和其他捞尸人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
第四天夜里,我捞起一对紧紧相拥的母子。母亲的手臂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弯曲着,将约莫三四岁的孩子护在怀中。孩子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湿透的毛绒兔子。
那晚我坐在船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作业时哭了。黄河在月光下泛着银光,温柔得像是能抚平所有伤痛,但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它仍会继续吞噬、继续奔流。
活下来的人
这份工作最沉重的部分,是将遗体交还给家属的时刻。
2012年,我捞起一位跳河轻生的年轻女子。她的丈夫赶来时,没有哭喊,只是轻轻抚摸着妻子泡得变形的脸,低声说:“你冷吗?我们回家。”
一个月后,我意外地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位丈夫发起了一个黄河沿岸心理援助热线的报道。他在采访中说:“我失去了最爱的人,但也许能帮别人留住他们的爱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有些故事看似终结,却可能在另一个人那里获得延续。
河边的守望者
二十三年,我捞起了超过三百具遗体。每捞起一具,我都会在河边坐一会儿,点一支烟,让烟雾随风飘散。老伙计们说这是我的仪式,其实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将刚刚结束的故事在心里安放妥当。
黄河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捞尸人,我们大多沉默寡言,皮肤被河风吹得黝黑粗糙。我们不是英雄,只是一群试图从水中打捞尊严的普通人。
有人问我怕不怕,说实话,怕的不是遗体,而是那些遗体背后破碎的生活、未竟的誓言、戛然而止的爱。
未说完的故事
去年,我捞起一个漂流瓶,里面塞着一张字条:“妈妈,黄河真的能带到大海吗?我会变成一条鱼去找你。”字迹稚嫩,没有署名。
我将字条小心收好,放进一个铁盒里。那盒子里装着我在这些年中从遗体旁发现的零碎物件:一枚婚戒、半张照片、一封未寄出的信、一只儿童手表...
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一个未说完的故事。而我,或许是这些故事最后的听众。
黄河依然奔流,不知疲倦。我知道明天、后天、许多年后,仍会有故事随波而至。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温柔地打捞,让那些未说完的话,至少能被一双眼睛看见,被一颗心记住。
夕阳西下,我又该出船了。河水拍打船舷的声音,像是无数低声的诉说。我启动马达,向着那片浑黄的水域驶去——那里沉睡着无数秘密,也流淌着不息的生命。

1.《我在黄河捞尸的日子:每一具遗体,都有一段未说完的故事》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站长。
2.《我在黄河捞尸的日子:每一具遗体,都有一段未说完的故事》中推荐相关影视观看网站未验证是否正常,请有问题请联系站长更新播放源网站。跳转第三方网站播放时请注意保护个人隐私,防止虚假广告。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yingshizixun.net/article/399b5353f454.html